番銀:跨越重洋的海絲見證

漳州月港的興起,開啟了中國貨幣流通的“白銀時代”。圖為位於漳州龍海區海澄鎮的古月港碼頭。胡智勤 攝

漳州軍餉銀幣(資料圖片)

1752年西屬墨西哥的8Real雙柱地球幣(資料圖片)

宣統三年大清銀幣(資料圖片)

小朋友在漳州市博物館數字展廳欣賞番銀數字展品。趙文娟 攝
這個暑期,“瓷影銀光——漳州海絲貿易瓷器與銀幣特展”走進武漢市博物館、太原市博物館,向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城市展示獨具漳州特色的海絲遺珍。
明隆慶元年(1567年),僻處海隅的漳州月港一躍成為當時唯一合法的民間海上貿易始發港。在這裡,海舶鱗集,商賈鹹聚,東西交融,瓷器、紡織品、茶葉等貨物通過月港輸出海外,在販回海外物産的同時,也換回了大量外國銀元,閩南人稱之為“番銀”,由此開啟了中國貨幣流通的“白銀時代”,對中國的經濟、文化、民俗産生了深刻影響。
“歷代興盛事,盡在錢幣中。”“白銀時代”早已隨歷史車輪滾滾而去,但通過一枚枚斑駁的銀幣,我們仍能窺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明清中外海上貿易的盛況,領悟貨幣政策對王朝興衰的深遠影響。
西風東漸的番銀
16世紀初,隨著新航路發現與葡萄牙人東來,大明朝捲入全球化貿易的浪潮。據文獻記載,葡萄牙人最早抵達漳州海面是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此後,葡萄牙人在漳州海面持續進行隱藏式貿易,長達30年之久,並且曾經在九龍江口浯嶼島建立貿易居留地。
明隆慶元年(1567年),朝廷開放部分海禁,于月港開設“洋市”,“準販東西二洋”,月港成為當時唯一合法的民間海外貿易港口。漳州的瓷器、紡織品、茶葉等貨物通過月港源源不斷輸出海外,換回了大量外國銀元。明代學者張燮《東西洋考》記載:“東洋呂宋,地無他産,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即有貨也無幾。”
“最早輸入漳州的番銀,就是西班牙在拉美屬地所鑄造的塊幣。”福建省錢幣協會理事、漳州文史專家林南中説,塊幣因其重量相對穩定、成色標準化,可以按枚點數、論枚計值,便於百姓交易,很快在閩南地區廣為流通,被老百姓形象地稱為“鋤頭楔子銀”。《天下郡國利病書》亦有載:“西班牙錢用銀鑄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今多用之。”
西班牙銀元自1535年手工鑄塊幣開始,至1732年半機制鑄造的雙柱地球銀幣,再到1772年更加規範的西班牙國王雙柱銀幣,因製作規範、規格統一、便於交易與攜帶,一直是當時世界貿易的主要貨幣。“在我國,‘一塊’也稱為‘一圓’,正是由西班牙銀幣單位而來。”林南仲介紹,西班牙銀元深刻地影響國際貨幣體系,像雙柱地球銀幣,正面圖案為王冠覆蓋下的東西半球,而兩側是西方神話故事中的大力神海格力斯之柱,柱上有卷軸纏繞,呈“S”形,當今貨幣名稱前的貨幣符號“$”便是由此而來。
自16世紀末起,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加速擴張,有“海上三駕馬車”之稱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貨幣持續不斷地流入閩南,以18、19世紀的鑄幣輸入較多。《清朝文獻通考·錢幣考四》記載:“至於福建、廣東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錢……閩、粵之人稱為番錢,凡荷蘭、佛朗機諸國商船所載,每以數千萬元計。”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大量鑄造精巧,重量、成色統一的外國機鑄幣輸入幣制落後的中國,並由沿海深入到內地。墨西哥“鷹洋”、日本“龍洋”、英國“站洋”、法國“坐洋”、美國“拿花”等外國銀元相繼進入我國貨幣流通領域,各霸一方,加劇中國幣制的複雜。在閩南一帶以墨西哥“鷹洋”、日本“龍洋”、英國“站洋”的流通使用量較大。
從16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在長達將近400年的時間裏,大量番銀不斷流入閩南。林南中説,目前在閩南地區已發現的番銀,來自西班牙、荷蘭等歐洲殖民大國,東南亞以及拉美地區和非洲的模里西斯等共計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時間跨度之長、數量之大、國別之眾、版別之多甚為少見,在世界貨幣發展史上可謂獨樹一幟,形成極具地域特色的貨幣流通現象。
推動中國幣制改革
“明朝初期,貨幣流通為錢、鈔並行,朝廷鑄錢幣,而禁止金銀作為貨幣進入市場。”龍海海絲文化研究會會長江智猛説,1567年至1644年,從漳州月港流入中國的白銀總數約為3.3億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産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全國的一半以上。月港貿易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幣值計算方式與計算單位,從“銀幣”重量計算向“銀圓”幣值計算轉變,並以白銀作為通用貨幣,換取實物,開啟了中國的“白銀時代”。
白銀的大量積累和流通,還推動了“一條鞭法”賦役制度改革,將原來民間繳納的複雜賦稅、勞役,統統折算成銀兩,由“實物稅”變成“貨幣稅”。農民拿穀物、絲綢賣給商人,換成銀子上交。這大大提高了稅收效率,充實了國庫財政,同時推動了白銀貨幣化進程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清道光時期,我國商品經濟已有明顯發展。然而,作為流通和支付手段的紋銀,仍採取分散、自由鑄造的方式,在全國沒有統一的規格,重量、成色、平砝各異,每一次支付都需要經過鑒別成色、稱重等複雜手續,無法滿足資本週轉迅速的要求。商品市場上亟需成色、重量和規格標準統一的銀鑄幣。
與此同時,大量規格統一、價值穩定、易於攜帶和儲存的番銀在市場上流通,成為閩南市場主要的交換媒介和價值尺度,出現“番銀之用,廣于庫銀”的現象。
“然而,外國銀元含銀量為90%左右,市場價值高於實際價值。”林南中説,許多西方國家商人將銀元帶入中國後,與“十足”紋銀兌換再運往國外,利用二者之間的差價獲取豐厚利潤,造成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鴉片戰爭期間,外國商人通過向中國大量輸入鴉片,換取了大量白銀,鴉片戰爭結束後的鉅額賠款使中國白銀外流更加嚴重。
據史料記載,鴉片戰爭前後的40年間,中國白銀流出總量達4.5億兩,幾百年的財富積累消散殆盡。白銀愈少,銀價愈高,造成“銀貴錢賤”的狀況,出現了足以引發經濟崩潰的“銀荒”。19世紀初,制錢1000文可兌換白銀一兩,到1849年,制錢2355文才能換銀一兩。白銀短缺,銀價大幅上漲,而老百姓仍然要從商人手裏購買白銀,以繳納各種賦稅,導致社會矛盾不斷激化。
面對“銀荒”肆虐,林則徐曾主張“自鑄銀元”,以自鑄銀元取代洋銀,並對貨幣問題提出“貴在流通”的看法,但遭到道光皇帝的拒絕。直到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之洞在廣東設銀元局鑄銀元成功,開啟了中國從“銀兩制”過渡到“銀元制”的歷史。因所鑄銀元鐫有龍形,故稱“龍洋”。
江智猛説,“龍洋”發行,一時給清廷帶來了久違的銀錢穩定、商貿復蘇、朝野振奮的良好發展局面。但幾年後,一些地方便自行其是,所鑄銀元純度下降,重量銳減,很多地區又恢復為銀兩時期的稱重剔雜交易方式,國家幣制繼續混亂。
在朝廷有志之士嘗試自鑄銀元,挽大廈于將傾之際,漳州在“龍洋”鑄造之前,也出現我國早期的地方自鑄銀幣——漳州軍餉。該幣成色98%,直徑在38至40毫米之間,重量在21至23克之間。正面上方橫書“漳州軍餉”,下有草書花押,背面上橫書“足紋”,下書“通行”。林南中説,在當時,漳州軍餉仍屬於手工打制幣,製作較為古樸拙巧,但鑄幣大小、重量、成色等都受到番銀影響,同時融入了中國文化的書寫及花押特色。
“白銀大量流入為東南沿海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貨幣支援,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明朝的財政壓力,也助推了中國貨幣體系的變革;另一方面,帶有經濟侵略性質的白銀流入也造成了通貨膨脹、貨幣體系混亂和社會不公等消極影響。”林南中説。
融入閩南生活文化
清朝宰相蔡新曾這樣形容番銀在閩南的地位:“若一禁止,則船皆無用……以商無貨,以農無産,勢將流離失所,又棄民間千百生民之食矣。”可見,清朝時期,海外貿易已與閩南百姓生計緊緊聯繫在一起。
“在漳州,人們買東西問‘多少錢’,都是説‘多少鐳’。這個‘鐳’字,就是從西班牙貨幣單位‘REAL’而來。”林南中説,西班牙銀幣在明末開始流入漳州並逐漸廣泛使用,貨幣單位在西班牙語裏稱為“REAL”(瑞爾,縮寫為R),按重量不同,分設有8R、4R、2R、1R、1/2R五種不同幣值,主幣為8R。各種不同幣值的銀元,極大方便商品交易和流通。於是這種閩南語讀音為“鐳”的銀元就漸漸流通開來。由此足見番銀的流通和使用,對漳州的社會經濟産生了巨大影響。
從清中葉至民國初期,漳州的廣大地區官方以及民間交易、納稅等經濟活動,大多以番銀作為結算幣,這從當時的銀票、借據、地契以及文書中大量使用“佛銀”“佛頭銀”“英銀”等貨幣名稱可以得到印證。
可以與此印證的,還有散落在漳州各處的寺廟碑記。在龍海區角美鎮東美村東美宮立有一塊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捐修碑記》,碑文內容有“景利捐佛頭銀壹百捌拾大元、明蓼捐佛頭銀壹百陸拾大元……華封馬劍貳拾元……天生馬劍陸元”等字樣;在詔安縣汾水關長樂寺,一塊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石碑“重建分水關觀音亭碑記”,上面鐫刻62個捐款人中,捐獻銀兩的佔11人,其餘51人都是捐獻銀元;在薌城區官園威惠廟有一清嘉慶六年(1801年)的石碑,上面的捐款數額都是銀元,其中許多捐資額使用到“角”幣。“當時中國還處於銀兩制時期,説明漳州以‘角’作為貨幣單位的使用在國內開了先河。”林南中説。
番銀除了用於經濟活動外,因其具有保值功能,幣面上又大多鑄有帝王頭像,百姓認為可以鎮災辟邪,因此將番銀賦予民俗功能,融入日常生活中。
“現在,在漳州許多地方,還保留著女方都要用‘七連貫’吊在轎子前,作為嫁粧之一的習俗。”林南仲介紹,所謂“七連貫”,就是用7個外國銀元焊成一串銀鏈子,老百姓認為可以避災驅邪。用於製作“七連貫”的番銀多達上百種。到小孩子滿月時,這條“七連貫”銀鏈要挂在小孩子的身上,表示吉祥,寄託讓小孩健康成長的美好祝願。
此外,女子出嫁時,裝嫁粧用的箱子要放置銀元來“壓箱底”。番銀還被改做成頭飾、紐扣等民俗用品,常常被用於陪葬和窖藏。這樣的風俗習慣至今仍在漳州許多農村地區存在。
番銀不僅深深影響了漳州人的日常生活,也在閩南地區形成獨特的番銀文化。
今年58歲的林南中,20多年來一直致力於記錄、推廣番銀文化,通過多種渠道收集了30多個國家的七八百枚番銀,並較為系統地梳理漳州番銀的發展歷史,出版了《閩海幣緣》《漳州外來貨幣概述》等書籍。他帶著這些故事走進圖書館、校園、直播間,開展番銀相關主題講座,讓那段塵封的歷史躍然眼前。
“番銀文化作為漳州海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更多研究和傳播。除了在漳州市博物館的海絲廳有固定陳列外,番銀展也是我們館對外交流展覽的一個重要項目。”漳州市博物館館長李海梅介紹,目前,漳州番銀展已到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銀川、武漢、太原等十幾個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城市交流展出,讓閩南海絲故事傳得更遠。
一枚枚跋涉千里的銀幣,承載著我國古代海上瓷器貿易的艱辛與輝煌,見證著中外貿易的發展與繁榮,也昭示著在時代洪流的推動下,世界各地聯通與互融的腳步從未停歇,並將繼續向前。(記者 趙文娟)
聽海
白銀時代繽紛海絲
大航海揭開全球化的大時代,滲透到世界每個角落的貨物貿易,讓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無遠弗屆,更加繽紛多彩。
近世數百年全球貿易,白銀是主要的結算貨幣,亮閃閃的銀幣(銀兩),是交易各方共同接受的硬通貨。
在古代東西方,白銀都是財富的象徵。但歷史上,白銀既曾折射過商品經濟發展的榮光,也承載過落後挨打的屈辱。
1005年1月,北宋與遼國在澶州訂立和約:遼宋約為兄弟之國,宋每年送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宋遼以白溝河為邊界。因澶州(河南濮陽)在宋朝亦稱澶淵郡,故史稱“澶淵之盟”。鴉片戰爭,中國戰敗。1842年8月29日,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其中涉及賠款一條雲:大清國向英國賠償鴉片煙價、商欠、軍費共二千一百萬銀元。此後,多個不平等的條約,皆涉及中國以白銀賠款的條款。特別是《馬關條約》,中國被迫向日本賠償軍費白銀2億兩(約合2.3億美元),這筆鉅額賠款加重了中國人民的負擔,同時加速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中國進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16世紀開啟的白銀時代,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是早期海上貿易的“三駕馬車”,與東方大明帝國商業往來日益頻繁,特別是月港被辟為合法的外貿門戶後,海上貿易更為活躍。
全球白銀産量自1600年起為12萬噸之巨(甚至更多),産量一半歸於亞洲,其中大部分無疑流入了中國。國內外學者均認為,中國在明清之後成為全世界白銀的“秘窖”,這是無可爭議的共識。而生生不息流動的白銀,是中國經濟的白色血液,牽動中國經濟的神經,造成一次次興奮與痙攣乃至紊亂。
白銀與明朝的興衰息息相關。究竟是白銀流入決定了帝國命運,抑或是帝國自身的走向影響了白銀流動?真實的歷史是無數個體互動的結果,白銀命運與帝國興衰之間也是如此。
16至18世紀明清海外貿易非常發達,可以説是當時海外貿易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人們從明清時期中國吸收的海外白銀量能看出一些端倪。從1567年隆慶開關起到1800年這233年中,每年從外國輸入中國的白銀皆超過200萬兩!而明代國內白銀的年開採量只有8萬兩。
從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到崇禎十三年(1640年)的80餘年間,澳門以其特殊的海洋貿易港口的地位,為明朝輸送了大量的白銀,填補了明朝本身白銀生産的不足,解決了明朝的“銀荒”。
無論是從貿易體量來看,還是從貿易結構來看,澳門已經成為16世紀下半葉至17世紀上半葉全球貿易體系的中心。隆慶年間,政府開放海禁,民間的海外貿易開始繁榮,澳門憑藉著其在當時的國際經濟地位,更是將明朝捲入了全球化經濟的歷史新格局。當時,以澳門為中心的南中國海上轉口貿易,已經形成了四條重要航線,即:澳門—果阿—裏斯本的亞歐航線,澳門—長崎的遠東航線,澳門—暹羅—望加錫—帝汶的南洋航線,澳門—馬尼拉(呂宋)—墨西哥/秘魯的太平洋航線。
歷史學家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在《葡萄牙帝國在亞洲》一書中説:“這裡(澳門)是中華帝國最繁榮的港口,僅葡萄牙人每年就從這裡運走五萬三千箱絲織品,各重十二盎司的金條三千二百個,七擔麝香、珍珠、砂糖、陶器。”
貨物外輸,白銀流入。那麼,由澳門輸入的白銀有多少呢?僅是從馬尼拉通過澳門流入明朝境內的白銀,從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開始,每年最低以200萬兩計,並呈逐年上升趨勢;而澳門至長崎的航線開通後,從1557年開始,每年由日本輸入明朝境內的白銀高達450萬兩,即使是到了崇禎九年(1636年),因為德川幕府對葡萄牙商人的不信任和驅趕,這條遠東航線的貿易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由長崎輸入澳門的白銀也有235萬兩。上述數額,還沒有把澳門—果阿—裏斯本的亞歐航線、澳門—暹羅—望加錫—帝汶的南洋航線的貿易額計算在內。
自16世紀末起,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加速擴張,其時,漳州九龍江下游的月港也迎來其最為風光的時代。“海上三駕馬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貨幣持續不斷地流入閩南,以18、19世紀的鑄幣輸入較多。《清朝文獻通考·錢幣考四》記載:“至於福建、廣東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錢……閩、粵之人稱為番錢,凡荷蘭、佛朗機諸國商船所載,每以數千萬元計。”
一位學者説,以絲綢、瓷器、茶葉、漆器等明朝特産在歐洲、日本等上流社會的暢銷度來看,當時世界生産的半數白銀都流入了中國,是毫無疑問的。
明朝在福建開放對外貿易,滿足了國內商品尋找和出口國外市場的需求,並且為帝國帶來了豐厚的商業利潤,隨著絲綢、茶葉、瓷器源源不斷地出口海外,歐洲、美洲的白銀如流水般進入明帝國。
相關資料顯示:從1567至1644年間海外流入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3億兩,相當於當時全球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故而明朝也就有了“白銀帝國”的稱號。鉅額的白銀緩解了明帝國的財政危機,為後世的張居正改革和萬曆三大徵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但歷史的發展邏輯十分詭秘,由於鉅額白銀大部分流進官僚的口袋,明後期國庫竟日益空虛,農民起義頻發,女真族趁機崛起,成為明朝滅亡的最後掘墓者。
在銀本位時代,白銀一直是世界貿易主要結算工具。據統計,1550—1800年的大約250年間,中國通過外貿共獲得了大約12億兩白銀,佔了這段時間內世界白銀總産量的一半左右。清朝代替明朝後,經濟和海外貿易恢復發展。1689年,英國與中國在廣州正式通商,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國。中國向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出口茶葉、絲綢、瓷器等,維持了此後100年以上的貿易順差地位。1820年,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32.4%多,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賺取了大量的白銀外匯。但是,從1840年到1906年,由於清政府腐敗無能,屢屢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中國一共賠付13.2億多兩白銀,相當於1901年清政府財政收入的11倍。這60多年,如天文數字的賠款,足以抵銷了明清時期流入白銀的總和。
天下興,社會穩,則經濟增長加快,銀子流通加速。天下亂,則經濟增長滯緩,銀子流通慢。作為商業文明的貨幣載體,明清時期,白銀對世界貿易的發展,無疑起了積極的助推作用,具有獨特的金融屬性和國際流通功能。
閃閃白銀,映照海絲繁華,折射商業文明盛況。在海絲拓展中凸顯功能的白銀時代,顯然是文明互動、和平交流的共贏時代,而不像戰爭帶來的白銀賠款那麼野蠻,那麼令人憎惡!
在全球一體化浪潮絕不會停止、世界維持多極化格局的時代,白銀的功能雖然不再,但商業文明之光、國際貿易之光,仍如白銀一般耀眼,仍將照亮各大洲人們的美好生活。(劉益清)
掃碼關注中國福建微信

掃一掃在手機上查看當前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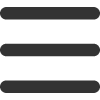

 閩政通APP
閩政通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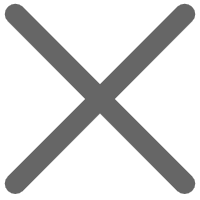

 閩公網安備:35000899002
閩公網安備:35000899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