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霉菌和农作物的攻防之战

春耕期间,平潭农户在种植马铃薯。 江信恒 摄

丰收季节,平潭农户在采收马铃薯。 江信恒 摄

被晚疫病菌感染的马铃薯 受访者供图

刘裴清在收集感病辣椒。受访者供图

科技工作者在实验室观察疫霉菌。 记者 林霞 摄
疫霉菌有多可怕?由其侵染引起的作物疫病,是一种毁灭性病害,每年给我国农业生产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几百亿元。
马铃薯晚疫病、大豆疫病、辣椒疫病,是我省发生危害最严重的三大作物疫病。
自1998年起,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省植保植检总站与海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北京汇思君达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组建了“作物重要疫病监测与防控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组,盯住重大作物疫病的成灾机制,25年孜孜以求,在病害监测预警手段、病害防控技术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不久前,省政府下发关于2021年度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该项目获得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从马铃薯晚疫病说起
3月16日,记者来到平潭润丰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马铃薯一体化播种机在田间缓缓驶过,施肥、打药、播种、覆膜一气呵成。“今年种了600多亩,这里也是平潭最大的二季作土豆主产区之一,年产量近千吨。”基地负责人刘守成说。
刘守成是一名山东汉子,2003年来到海岛种田时,平潭人还将其当作一件稀罕事。“我到平潭岛一看,农村这么多闲置土地,租金还便宜。再一琢磨,这地都是沙质土壤,适宜种植,农作物可以种两季。”于是,他把老家寿光市优质的马铃薯、萝卜等品种引至海岛,从一两百亩开始尝试,逐渐扩大到上千亩地。
然而,种植马铃薯有一件特别糟心的事,就是遇上晚疫病。“晚疫病有多可怕?‘爱尔兰大饥荒’听过没?19世纪中叶,一场在欧洲大流行的马铃薯晚疫病,导致爱尔兰上百万人饿死。”刘守成向记者科普道。
2018年春节后,马铃薯田间就发生了一次特别严重的晚疫病。彼时,岛上阴雨不断,加之大风天气,病斑沿叶脉侵入叶柄及茎部,多片种植区域的叶子被浸染变黑呈湿腐状。
“这种病菌不仅会以菌丝体在薯块中越冬,借助雨水或灌溉水传播,病叶上的孢子囊还会渗入土中侵染薯块,形成的病薯就成为翌年主要侵染源。”下乡指导的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李本金在记者身旁解释道。
“能否直接下‘猛药’?”记者忍不住问道。
李本金直接否决了:“在不清楚抗病基因作用机制的情况下频繁滥用药物,日积月累,不仅对作物有害,也会产生抗性。”
那么,面对这一沉疴,该如何开方?
答案就在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首先要摸透这个病菌‘样貌’,顺藤摸瓜,才能对症下药。”李本金说。
记者跟随着李本金来到实验室。她先是取出两块现切的分别只有7~9毫米厚的感病薯块,再将染病的叶子夹在当中,在合适的温度下培养于生化培养箱中。“5天后,晚疫病菌就会从染病的叶子蔓延到两片薯片上,再经过两次纯化处理,就能有效分离出晚疫病菌纯菌种。”她说。
“染病的叶子或薯块中,除了晚疫病菌,还有其他种类的菌。要单独分离出晚疫病菌,必须找到晚疫病菌‘爱吃’而其他病菌无感的‘食材’。”李本金补充道。
早在2011年,李本金等人发明的“一种分离马铃薯晚疫病菌的改进方法”就获得了发明专利证书,该方法将马铃薯晚疫病菌分离效率从10%提升至98%。李本金将其命名为“薯片夹心分离法”。“特别是从省外采集的染病叶子或薯块,已经烂到不行了,人工挑不出晚疫病菌,而采用‘薯片夹心分离法’就能将其精准分离出来。”
这只是“作物重要疫病监测与防控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组取得的成果之一。
“摸透一个病菌远远不够,我们要做的是对其进行群体结构系统研究。”李本金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老祖宗的智慧是项目组科研设想的重要起点。项目组决定广撒网,采集不同地区的晚疫病菌。
从1998年到2020年的每年3月,项目组成员都要一起下田。最近的,是距离市区约60公里的永泰县;最远的,则是距离福州约2500公里、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克山县。这些年来,他们一共去了12个省(区、市)的相关种植区。
处理拿回来的晚疫病菌,也是一件繁杂的事。“首先要预备足够量的固体培养基,为晚疫病菌准备‘温床’。”李本金说。
分离实验,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大部分拿回来的染病叶子或薯块,团队成员选择将晚疫病菌直接挑出来,放置在固体培养基,待长出来时,再继续清理其他杂菌,如此反复,直至得到纯的晚疫病菌。也有一部分“烂得厉害的”,需要使用“薯片夹心分离法”。“‘薯片夹心分离法’尽管精准,但一次分离实验需耗时近半个月。每次采集的晚疫病样品有大几百份,等不及了,‘新鲜的’只能保湿完直接挑。”李本金说。
除了3月,8月也是“采收”晚疫病菌的好时节——从上午8点到晚上12点,技术团队十几号人围着挑菌。人工挑菌,失败是常有的。“挑出来的菌放在固体培养基,如果杂菌长得太多,晚疫病菌就挑不出来。”李本金说。
如此往复,团队最终从不同马铃薯品种的田地里采集了1325个晚疫病菌株!
正确识别敌军,是战役胜利的第一步。“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晚疫病菌株对马铃薯R3抗性基因有毒性,对R4、R7和R1的毒性频率也都在60.0%以上,说明这些抗性基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李本金说。
项目组发现,由于马铃薯种植品种比较单一,晚疫病菌株受选择压力产生变异,逃避了马铃薯R3、R4、R7、R1等抗性基因识别,从而导致品种抗性丧失,病害暴发。“这些抗病基因抗性丧失,源于晚疫病菌性状变异,即晚疫病菌‘乔装打扮’,逃避了作物的抗病识别。”李本金解释道。
项目组还发现,甲霜灵类药剂已失去对晚疫病的防治作用。而与此同时,菌株对R9抗性基因的毒性频率最低,仅为9.9%,“说明了具有R9抗性基因的马铃薯品种的抗性优越性,这一发现在抗晚疫病品种育种及品种布局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破译密码 发出警报
马铃薯晚疫病、大豆疫病、辣椒疫病等病害,具有发病快、变异快、流行快等特点,防控一直比较困难,被称为“植物瘟疫”。25年来,在马铃薯晚疫病、大豆疫病、辣椒疫病之间辗转,项目组努力想要撕开一个口子。
“作物疫病高效防控,是我省农业生产的重大需求。但最开始,福建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存在病害成灾及病菌变异机制不明、病害预警监测手段技术落后、病害防控措施缺乏针对性等问题。”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刘裴清说。
项目组将对付马铃薯晚疫病菌的成功经验也应用在大豆疫霉菌、辣椒疫霉菌上,逐步揭开在肉眼不可见的微观世界里,疫霉菌“攻击”和植物“抵抗”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与马铃薯晚疫病菌一样,大豆疫霉菌、辣椒疫霉菌也是“吃货”。
大豆疫霉菌爱“吃”的是大豆叶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技术团队这一次采用的是“叶碟法土壤诱捕”——在从染病的大豆种植区取来的土壤中加入含药无菌水后,加入翠绿的感病大豆叶碟;一个星期后,土壤中的大豆疫霉菌就会被叶碟所吸引,逐渐将叶碟侵染。此法将大豆疫霉菌分离效率从20%提升至80%以上。
对辣椒疫霉菌的分离实验与此类似,只是辣椒喜好的“食物”却是黄瓜,而此法则将辣椒疫霉菌的分离效率从70%提高到93%。
2006年,随着国际疫霉菌基因组测序的完成,项目组成员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王源超教授也从疫霉菌基因组入手,探索揭示病原菌致病机制。下乡采集马铃薯晚疫病菌的那些年里,项目组还在不同月份分别采集了不同地区的大豆疫霉菌和辣椒疫霉菌,逐渐建立起病原菌数据库。
“我们发现,病菌交配型多样化、高抗药性、高毒力菌株成为优势菌群等引起群体结构演变,是疫病暴发成灾的主要成因。”王源超说。
他们破译了基因密码——对福建、黑龙江、吉林、安徽等省大豆疫病发生地区采集分离的546个大豆疫霉菌株进行群体遗传结构分析,发现这些病菌具有丰富的基因型多样性和显著的地区差异,病菌主要以近亲交配或无性生殖的方式繁衍。
他们还基于研究,发出更多警报。
项目组对从厦门、泉州、漳州、宁德等城市采集分离的300个辣椒疫霉菌株的交配型测定,明确了辣椒疫霉菌群体为多种交配型共存,意味着该病菌在田间产生卵孢子,发生基因重组,形成致病力更强的新菌系。“也就是说,疫霉病菌会在土壤中越冬,成为下一季的初侵染来源,造成下一季大流行。”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翁启勇研究员说。
项目组还发现,“我国大豆疫霉菌毒力类型复杂,其中Rps7已被多数菌株克服,基本丧失了应用价值,而Rpslc和RpsIk在抗大豆疫病育种及品种布局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福建辣椒疫霉菌不同群体间则存在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提示抗疫病品种选育应以水平抗性为主,品种布局上应多样化”。
……
“逃避抗病基因的识别是病菌致病性变异的主要途径,是导致作物抗病性丧失的主要原因。”王源超说。王源超团队还在国际上首次克隆了疫霉菌无毒基因Avr3b和Avr1d,并发现作物基因中出现点突变、大片段缺失、基因沉默,是导致作物抗病性丧失的变异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组还研制出马铃薯晚疫病菌、大豆疫霉菌及辣椒疫霉菌等重要疫霉菌新一代可视化快速检测技术,比国内外原有技术的检测准确率提高了3至5个百分点,检测灵敏度提高了2至6倍。
“这些研究结果为开展病害监测、筛选抗病品种及防控技术研发提供了理论依据。”刘裴清说。
把科技送到田间地头
从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实验室出发,记者再次回到平潭润丰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
这一次,刘守成带着记者来到田里一台1米多高的机器前:“这家伙可对空气温度、空气湿度、雨量等要素进行全天候现场监测,并通过4G无线传输至平台存储、分析。种植马铃薯,再也不怕晚疫病了!”
2018年起,项目组成员北京汇思君达科技有限公司指导刘守成安装了马铃薯晚疫病检测设备,构建冬作马铃薯晚疫病的预警监测体系,实现了病害早期准确预报。
刚开始,这套仪器曾“水土不服”。“仪器的监测预警系统最早是基于比利时马铃薯晚疫病设计的,需要结合我国冬作马铃薯种植栽培特点,对原系统进行改进和提升。”在此后的一年中,李本金等人多次往返福州和平潭,根据气象观察数据,最终摸索出“在晚疫病菌第四代第一次侵染时,进行第一次喷药防治”等结论,实现仪器本土化、程序化、智能化。
除了平潭,这套仪器如今也已在宁德霞浦等地安了家。
项目组通过多点实地调查对比,马铃薯晚疫病短期预测预报准确率达97%以上。“相较于传统防治,该系统能准确确定有效的防治时间、防治次数,指导种植户科学合理选择药剂类型。”李本金说。
按照此方法,化学杀菌剂用量也减少了。“现在栽种马铃薯,不仅能有效控制病害发生,出土的产品还能达到A级绿色食品标准。”刘守成喜笑颜开。
25年来,类似这样的科技成果越来越多地被送到田间地头。
大豆有了“定制的新衣”。2008年起,项目组筛选出用于防控大豆疫病的烯酰吗啉、福美双与恶霉灵混配的种衣剂及使用方法,创建了大豆疫霉根腐病种子处理技术。此举令防控效果提升了10%至30%。
克制疫霉菌也有更多的奇招。项目组筛选出6株防治马铃薯晚疫病、大豆疫病及辣椒疫病的高效生防菌,还创建了以亚磷酸盐作为抗诱剂及使用方法,对马铃薯晚疫病防治效果良好。
更多的“优等生”脱颖而出。对从台湾亚蔬-世界蔬菜中心引进的6个抗晚疫病番茄品种、8个抗疫病辣椒品种、6个菜用大豆抗疫病品种进行筛选,选出了对福建马铃薯晚疫病、大豆疫病及辣椒疫病主要优势菌系均具有优良抗性的品种共12个。
与此同时,种植户种马铃薯、大豆和辣椒也更有讲究了。
“我们构建了以种子处理为核心的大豆疫病防控关键技术、以监测预警为核心的马铃薯晚疫病防控关键技术和以诱抗剂为核心的辣椒疫病防控关键技术。”项目组成员海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陈庆河教授说。
项目组还在我省首次构建了疫霉菌基于不同传播途径分类防控策略的技术体系,制定了疫霉菌致病性测定技术规范、作物品种抗疫病鉴定规程及作物疫病防控技术规范等地方标准。
“以亩产增产增收产值及农药使用节约成本计算,生产每季减少用药2~3次,农药的投入量降低10%~20%,平均每亩次增收150~350元,平均每亩次节省农药成本及人工费50~100元。”刘裴清算了一笔经济账。
自2015年起,项目成果在我省的8个设区市进行大量推广应用。据统计,2015—2020年期间,累计示范推广应用面积462万亩次,增收节支总额达10.6亿元。
不只“作物重要疫病监测与防控关键技术及应用”。当前,广大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对作物防疫进行深入探究,为涉及粮食安全的科技前沿问题先手把脉,更多科学技术成果在我省广袤的田野上渐次生效。(记者 林霞)
扫码关注中国福建微信

扫一扫在手机上查看当前页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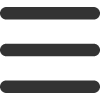

 闽政通APP
闽政通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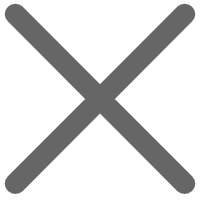

 闽公网安备:35000899002
闽公网安备:35000899002 


